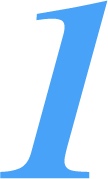中時遭暗算,報人余先生要把自己送出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二)
時間:2019-07-19 歷史與文化
 (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的這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先經由我的口再多說一說他。圖片來源自網絡)
(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的這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先經由我的口再多說一說他。圖片來源自網絡)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二。
---------------------------------
踏上征途,意味著重新面對余老闆——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的這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先經由我的口說一說他。
余先生為了參加抗日,中止了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學業深造,回到國内。因為海歸高知識份子的緣故,他投身軍旅就從少將開始編階,並依專長参與的都是跟政治任務有關的工作。他被派在陜、甘地區主持軍事或幹部訓練學校的政治部和教導部,還在蔣經國主領青年軍軍政時,當過他的政治部主任,也在蔣任中央黨部訓委會主委時當過他的主任祕書。實際做了哪些事不常聽他說起,但明顯與後來的政工不一般,應當檔次更高一些,是智庫智囊的那一種。
抗戰勝利後余先生被派往東北,先後在東北行營、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政治部主任,處理接收復原的工作,並且創辦《中蘇日報》。這是他與報紙結緣的開始,不過這可不是個愉快的經驗,因為報社被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渗透,為東北形勢的逆轉,起到過一定的作用。“接收大員”(1945年8月,抗戰取得勝利,國民政府派遣“接收大員”,接收敵偽資產)陳誠不諒解他,揚言要斃了他,使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活在這個陰影中,據說是蔣經國保了他。
由於我的父親同一時期也在東北行營任上校軍需官,雖然他們彼此没有隸屬關係,也不相識,卻因這個東北淵源,使我對余先生彷彿多了一份對前輩的認同感。而我與他的長公子余啟成,1947年同在瀋陽出生,在後來彼此的相處中也顯得比較易於接納。不過,我卻從未與余先生談過這個話題,我不喜攀附,我們之間好像也不需要扯上這層關係,因為它絲毫影響不到彼此該有的歡喜及該發的脾氣。
東北的陰影使余先生在來台之初度過了一段困頓的日子,他起初在經濟部物資調節委員會編輯一份油印的商情匯刊,叫《徵信新聞》,漸漸變身為《徵信新聞報》。在擴展內容及製作其他新聞的過程中,工作同仁往往還受到採訪對象的調侃:“這又不是財經消息,你們幹嘛來採訪?”直到1968年,一個大氣、響亮、居世界前沿的報紙名稱——《中國時報》取代了《徵信新聞報》,經余先生之手昂然誕生了。
而就在半年前,這個原先以報導商情起家的報紙,剛剛破天荒改以彩色印刷,成為亞洲第一份彩色報,更是中文第一份彩色報。
 (余先生提筆寫下“同仁要有抱負,無私無懼,留下一部百年青史”。作者供圖)
(余先生提筆寫下“同仁要有抱負,無私無懼,留下一部百年青史”。作者供圖)
這兩件事在向世人宣告,余紀忠先生憑以往成功經營的經驗,對未來有强大的企圖心,也時刻充滿氣勢和活力。因此,我於1971年毛遂自薦,進了余先生門下。
余先生的父親早逝,由寡母於艱苦環境之中撫育成長,所以毅力過人。他是讀書人,受到中西高教薰陶,主見、理想,從來不缺,風骨、氣節,始終為念。處身在特殊的時空裡,辦報是非常辛苦的事,但也正因這樣的環境,才是成就“報人”身量的大好機會。
余先生遇到了這個機會,也把握了這個機會,但可惜沒有充份堅持和深耕下去。
在《美洲中國時報》所見的余先生,可說充分體現了第一代創業家的所有特質。籌備期間他完全親力親為,以73歲的高齡忙着定方向、想内容、覓人才、找廠房、看機器、買設備,馬不停蹄,席不暇暖。每天開會、奔走、苦思,住的是汽車旅館,吃的是麥當勞,跟部屬同甘共苦。余伯母偶爾陪他同來,卻被我們瞧見在摩鐵(汽車旅館)裡幫余先生燙衣服,有如尋常百姓家。有時完成工作,等到他就寢了,我和其他年輕人乘此空檔談天說地,喝上幾杯,可一大早就被余先生一一叫起,不許我們睡懶覺。其實這哪是懶覺,才臥倒而已,他可不管,新的一天開始,要繼續幹活!
開報以後還是一樣,不管在不在美國,指示與要求從沒停過,三不五時要檢討,隨時隨刻要改版。這個報紙内容飽滿,從五大張到十大張,有各個不同地方的版,各種不同屬性的版,三天兩頭改版,還要因應需要不時增加新的版。有美國本身的東南西北,有跨太平洋的台灣、香港地區,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各個特派點。這中間所有的協調運作、觀念溝通、人力整合,講求有效統一,他無不要關心、操心。那時候他用了幾個外來人挑大樑,又不放心,可找了自己“大麻煩”,哪能省事?
余先生自視甚高,除了他跟過的蔣經國以外,其他人全都不在他眼裡,特別是特務系統裡的人,他幾乎一個都瞧不起。偏偏余先生辦的報紙,總有些不那麼配合政策的地方,總有些新聞、評論讀來怒上心頭,這些靠打小報告吃飯的人當然對余先生和他辦的報紙不會客氣,我在台北的《時報》歲月也曾深刻領略,之後被“發配”來美也是拜此之賜。如今余紀忠居然到美國辦報,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不知會弄出個什麼“禍害”來,搞特別任務的那還不殺殺他的威風再說!
於是,《龍旗》雜誌出手了。
那是個沒有名嘴的時代,如今幫着執政者怒斥加修理反對派的行為,就是《龍旗》雜誌當年幹的事。
但是它不像名嘴展現在螢幕上,乃全然隱身在筆名之後,有如現代網民,搞不清打手是誰;只能推想來自某個可怕的權力部門,而且極可能、也極擔心會進一步採取什麼行動。
挑明了說,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當時中國國民黨主政的蔣經國政府稱此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無意中助長了政工系統的氣焰,趁勢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在國民黨政權危疑震撼之秋,負起如少康中興穩定政局之責,而獲得蔣經國某種程度的優容。《龍旗》雜誌便是受命於由“特務頭子”王昇上將主持的這個黨國“違章建築”,對《中國時報》有計劃地進行打擊和教訓的。
《龍旗》每一期都以長篇累牘嚴打《中時》和余先生,文字達到嗜血的程度,比起大陸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批鬥,猶有過之,充滿仇恨與恐怖。
那是1983年初的事,《美洲中時》開辦才幾個月,余先生在美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固然可說那是工作上的需要,但我很清楚,他因為《龍旗》現象,不想回台灣。
《龍旗》的文章每期都會從台北傳真到他手裡,余先生不逃避,看得仔細,並且讓大夥兒一起看。我們看了不禁破口大駡,但余先生很平靜,只是搖頭、嘆氣,卻未出惡言,照樣工作。
記得有一回開完會,在一個平價餐館用餐,聊起剛收到的《龍旗》,余先生憂心國内政局在“肖小亂政”之下更加倒退不堪,聊着聊着突以手擊桌,說:
“天瑞!就跟你一樣,我也找個學校,在美國待下來吧!”
當場把大家嚇了一跳,這可不是小事,《中國時報》老闆海外避禍,滯美不歸,代誌大條(閩南語“事情鬧大了”的意思)。他怎麼能跟把周天瑞送出國一樣,也把自己送出國!
在場的《中時》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可來了勁,當即表示很願意幫忙余先生安排學校,華府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和馬利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這兩所研究型大學都很合適,他們對余先生一定會非常歡迎。這話說得絕對沒錯。
由此可知,雖然大家認為兹事體大,但以那時的氛圍,倒也覺得不失為一個辦法。相信余先生不是脱口而出,而是真的想過。第一次我感受到,傲岸如他,也有無奈落寞的時候。後來聽他說甚至想關台北的報,留美國的報,那就更顯得慌了手脚,王昇真把他嚇壞了!
 (王昇(左)當年受CIA之邀訪美。作者供圖)
(王昇(左)當年受CIA之邀訪美。作者供圖)
實際並沒有這麼做。因為正在那時,王昇受美國CIA邀請來美訪問,回程特别彎到舊金山余先生住所,帶着禮物登門做友善拜訪。大概知道打得太過火也會出紕漏,藉此拜訪,心照不宣,好讓余先生放寬心情。果然,不久余先生就回國了。
其實,福兮禍之所伏,王昇受邀訪美促成了他的下台。他打別人小報告,别人還打他的呢。劉少康辦公室的行事早受非議,美國高規格邀訪以近乎國賓之禮相待,不知何所圖,他竟受之,不避嫌猜,豈不犯忌?5月,貶往聯訓部,9月,遠謫巴拉圭。王昇失勢,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王昇遭除,並不意味余先生就此安全上路。保守勢力不愁沒人接班,過了大約一年比較安穩的日子,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延伸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