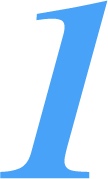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為什麽大英帝國明明早已崩塌,我們今天卻還在其股掌之間?”
時間:2021-12-29 經濟與科技

(人類學家與超布連群島上的原住民。圖片來源自網絡)
2020年6月,新冠疫情漩渦下的美國“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蔓延至英國,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聲浪叠起,英國帝國理工大學在壓力下決定放棄已經沿用了百余年的校訓:“科學是帝國的無上光榮和保障”(Scientia Imperii Decus et Tutamen)。
這一決定,再次將科學與帝國的關係帶入人們的視野。在五百多年的殖民史中,北大西洋殖民帝國將科學作為踐行“文明使命”、建構殖民統治正當性的載體,而亞非拉國家意識到科學本質上仍然是帝國支配殖民地的工具,晚近兩百年來的英美兩大全球性帝國則用科學來營造其世界性的文化霸權。
科學支撐帝國,帝國依賴科學,科學究竟如何賦予帝國以正當性?從歷史的縱深處,重新認識科學與帝國的密切關係,或可助益於我們自身的發展道路更具自主性和創造性。
一、作為帝國文明使命的科學:科學與帝國的興起
作為帝國文明使命的科學,是科學與帝國關係的第一種敘事。在這種輝格主義的進步視角中,科學是進步的源泉,帝國是科學的母體,科學為帝國征服披上了文明的面紗;西方世界孕育了智慧超常的傑出人物,秉持基於數學的精確科學思維,教化愚昧迷信的非西方世界,科學成就讓基督教歐洲自視在教育、知識、能力、理性和德性上,都比那些歐洲以外的“化外之民”高人一等,後者完全沒有理性的能力和知識的理解力,沒有能力像歐洲人繪制美洲地圖那樣繪制歐洲地圖;正是滿懷科學精神的歐洲人漂洋過海,“發現”新大陸,探索異域的自然景觀,觀察奇異的人文風俗,搜尋蠻族的食物、藥物和經濟作物的種植方法,運用先進的帝國科學改造落後、蒙昧、野蠻的帝國邊陲,履行帝國教化殖民地的文明使命。這裡的文明以“科學基督教”為核心,具有雙重意涵,既是基督教相對於異教徒的文明,也是科學相對於迷信的文明。
既然科學的興起與帝國的興起亦步亦趨,哪些歐洲科學屬於首要的殖民科學就至關重要,而這取決於哪種科學對於殖民擴張和解決殖民困境更有用。對法帝國而言,制圖學、氣象學、冶金學、經濟植物學更有用,也獲得更多財政投資。對英帝國而言,環境學、生物學和醫學最有用,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次之。帝國對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也以有用為依歸,比如19世紀晚期英帝國在其“巔峰時刻”才在印度開始科學技術教育,但也只是在地理學、測量學、植物學和醫學等有直接經濟效用的領域,旨在為帝國培養技術服務人員。

(圖片來源自網絡)
在五百年的資本主義殖民帝國史上,帝國是科學研究的引擎和樞機,塑造著科學知識的生產形態。殖民模式不同,科學知識的生產形態也不同,“文明使命”的色彩也深淺不一。
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人開創了以東印度群島為典型的貿易站帝國模式,在加勒比地區建立了依賴經濟植物學等科學支撐的種植園綜合體,種植園主和企業心理學家醉心於發明催眠術,以創造溫順的工業奴隸,這些都為後來的荷蘭英法所借鑒;西班牙人將新大陸變成了西班牙君主治下的美洲總督國,率先通過科學組織系統收集大西洋的水文知識和美洲的紡織術。但對伊比利亞人而言,對殖民地資源的控制和掠奪優先於“文明的使命”,粗糙的科學知識生產形態使其在殖民爭霸戰中落後於法英德。
在法帝國模式中,帝國是科學的主要資助人和科學機構的創建者,王室是科學的物質和智力資源的調度者,貿易公司的醫生為殖民者提供健康服務,兼任自然學家、植物學家和醫學家,遊走於全球的耶穌會傳教士也是自然科學知識的載體,向清政府索要的義和團賠償成為法國在中國的天文學和法國本土漢學經費的來源。法帝國首都巴黎變成了歐洲內部的國際科學中心,並把科技領先優勢一直保持到19世紀40年代。隨著英德科學的崛起,法蘭西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德國柏林學院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漸形成。當時的德意志帝國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但在其大學形成的政治學,在17世紀中期直至18世紀末,影響了整個歐洲。
在英帝國,帝國的貿易和擴張被視為科學知識的源泉。英帝國不斷擴張的邊疆,成為自然神學、自然哲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天文學、物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制度起源。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的帝國經驗,深刻影響了英格蘭啟蒙運動,英國的經濟生活、智識生活由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帝國上下、朝野內外的支持下,科學的各個分支部門快速發展,帝國如虎添翼,帝國向殖民地傳遞文明的使命感也隨之強化。
在作為帝國文明使命的科學敘事中,帝國是科學的護衛者,歐洲人憑借科學享有了宰制非歐洲人的正當性,並由此建構帝國統治的真理的合理性,歐洲以外的世界處於愚昧、落後、野蠻、迷信狀態,是歐洲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歐洲帝國的教化對象,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改造對象。沿著北大西洋兩岸不斷向外延展的科學邊疆,成為歐洲人心馳神往的帝國機遇。越洋帝國的興起,改變了歐洲人的政治視野,提升了歐洲人的文化信心,固化了歐洲人的文明使命感。
二、作為帝國控制工具的科學:科學與帝國的擴張
作為帝國文明使命的科學敘事,流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諸歐洲殖民帝國爭霸世界的時代。但是,科學與帝國的共謀,始終處在啟蒙運動與奴隸制共存的陰影之下,文明背後的控制從未隱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與世界的關係發生巨變,歐洲從世界的主宰者變成了美國的跟隨者,美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取代了英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共產主義革命的影響下,亞非拉國家開始反思歐洲霸權,反思文明面紗所遮蔽的科學與帝國的另一層關係。
20世紀50年代,隨著帝國史研究轉向韋伯主義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作為帝國文明使命的科學敘事受到廣泛質疑,作為帝國控制工具的科學敘事迅速成為主流話語,科學被視為帝國建構異族他者、構築支配-依附關係的工具。在這種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視角下,科學與帝國都是龐大的社會與政治工程,科學承載著歐洲人統治世界的大國夢想,科學革命與殖民帝國擴張的興起、征服和鞏固都密切相關。
在殖民帝國的興起階段,科學和醫學培育了帝國的航海技術和戰爭手段,蒸汽船的發明、奎寧的預防性使用以及航海、航運和採礦技術的出現是這一階段的關鍵。制圖學、水文學服務於保障帝國間和平和殖民航海自由的國際法,服務於帝國對殖民地領土、港口和貿易站的控制。殖民帝國秉持標準化、清晰化的極端現代思維,在地圖上所畫出的,既有不考慮殖民地本土傳統的領土分界線,也有對所謂無主土地的法權分界線,還有區分戰爭與和平、文明與野蠻的海洋分界線。線內是文明理性之地,殖民帝國之間保持和平,線外是野蠻蒙昧之地,殖民帝國之間互相廝殺。格勞秀斯等荷蘭自然法學家所主張的航行自由,就是從線內通往線外“無主之地”的殖民自由。殖民帝國還按照文化的分界線劃分勢力範圍,五大湖區這個“中間地帶”就是一個複雜多變的土著聯盟,西班牙與美國的混血兒在英屬美洲催生了文化混合區,新法國和新巴西則因為對奴隸勞動的依賴程度差異而成為完全不同的美洲社會。人類學向帝國提供了殖民地本土的文化與軍事情報,人類學家和醫學家在創造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的定型觀念上“居功至偉”,社會學家和科學史家學習人類學家,把自己想象成現代實驗室的陌生人,想方設法獲取殖民地的特定知識。西非“大米海岸”以婦女為主的水稻農民就是這樣被作為殖民地特定知識的載體,強行運到卡羅萊納等地的殖民種植園。

(圖片來源自網絡)
在殖民帝國的征服階段,熱兵器的革新,航海術的提升,讓歐洲國家長期保持對非歐洲國家的軍事和戰爭技術優勢。博丹所說的不可分割的主權,韋伯所說的壟斷針對特定領土與人口的合法暴力,也正是帝國最重要的兩大特性。帝國的殖民擴張過程,意味著對美洲印第安人和大洋洲土著居民的大規模種族清洗,對非洲人的殘酷奴役。就此而言,近代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根本就是一回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建構同時也是殖民帝國的興起與擴張,正如16世紀30年代脫離羅馬天主教神權統治的英格蘭所宣稱的:英國不再屬於任何別的帝國,英國是自己的帝國。民族國家及其特性具有鮮明的帝國基因,也正因此,帝國既具有國家的領土性,也具有超國家的非領土性,而科學則成為帝國超越歐洲本土民族國家邊界向全球擴張的新工具。
在殖民帝國的鞏固階段,鐵路、海底電纜和蘇伊士運河等溝通技術的革命將宗主國與殖民地整合起來,讓帝國統治得以實施。諸殖民帝國之間對於影響力和勢力範圍的激烈競爭,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經費。比如法國與亞洲的無線電通信研究,就是為了擺脫對英美海底電纜的依賴。
殖民帝國擴張所必需的天文學、氣象學、地球物理學、化學等精確科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軍事學、戰略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都依賴地球表面特定位置的資料收集,也都需要以整個世界為尺度才有意義。進而言之,科學的全球性正是帝國統治的內在要求,科學並沒有因為成為帝國的控制工具而受到破壞,反倒更加發展壯大,為帝國的擴張加入了自然的邏輯,為帝國的征服營造了正當性,為歐洲帝國主義提供了文化軟包裝,並且隨著帝國的擴張提升了自身的全球性。隨著冷戰格局的興起,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土崩瓦解,世界格局滄桑巨變。不過,盡管殖民帝國不復存在,但其霸權卻並未隨之消失,科學與帝國關係的第三種敘事,即作為帝國文化霸權的科學由此興起,並推動了發展話語的迭代。
三、作為帝國文化霸權的科學:發展話語的迭代
作為帝國文化霸權的科學,可以視為前兩種敘事的升級版,它建立在對殖民科學擴散模式的深刻反思上。擴散模式是殖民科學發展的三段論,在初級階段,殖民地為西方科學提供原始數據材料;在中間階段,殖民地與帝國之間形成正式的殖民依附關係;在最終階段,殖民地走向科學的獨立自主。在擴散模式中,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是中心與邊緣關係,科學從中心向邊緣直線傳播,歐洲是科學傳播的動力源,歐洲對世界的殖民發揮了漸進的拯救性的歷史作用,把歐洲科學傳遞到殖民地社會,後者只有通過歐洲科學文化的再生產,才能最終走上現代化之路。科學不再是具有宗教神聖性的帝國文明使命,也不是單純為了攫取殖民地資源的帝國控制工具,而是具有真理性、先進性和普遍性的知識體系,從而成為非西方社會很難擺脫的文化霸權。
這種殖民科學的擴散模式,堪稱20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並影響至今的現代化與發展理論的源頭。歐洲的科學就是整個世界的現代化與發展的引擎,這種作為帝國文化霸權的科學敘事曾經如日中天,卻在當代發展話語中逐漸隱匿起來。
發展話語誕生於資本主義霸權轉移的20世紀20至40年代,發展話語的競爭主要在英美兩大帝國之間展開。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蕭條的蔓延,人們對英帝國管理殖民地的能力產生了強烈質疑,英帝國因此將1895年至1940年的殖民地政策稱為“建設性的帝國主義”,將帝國的政策目標從“改善”變成“發展”,從以攫取殖民地資源為主、改善殖民地狀況為輔,轉向推動殖民地的發展,為殖民地提供交通、通信和科學政策扶持,刺激殖民地的商業和資本需求,充分開發殖民地資源,進而緩解帝國本土的失業問題,推動整個帝國的經濟發展。
在這個以經濟發展為關鍵詞的新殖民政策中,科學始終處於核心位置。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推動了帝國自然與社會科學的興起,殖民地成為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化學、農業科學、人類學和經濟學的樂園。科學研究由帝國政府資助,與自由放任無關,這是因為,科學既是打開殖民地的第一步,也是讓殖民地產品與帝國市場匹配的關鍵,其初衷還被標榜為培育殖民地參與國際科學進步和運行現代國家的能力,進而證明英帝國長期保持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包括專業研究所、學院、實驗室在內的大量殖民科學機構先是在帝國大都市建立起來,後來又轉移至各殖民地,英帝國的殖民部、市場局和殖民研究處是這一切的操盤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遭遇經濟危機,理想主義的發展理念與帝國主義的剝削再度融合,英帝國改變了小規模精英主導的科學體制,建立了涵蓋漁業、農業、林業、動物健康、錐蟲病、蝗災、殺蟲劑和經濟等議題的一大批殖民研究機構,在殖民地研究中心統籌下,招募大批科學家,評估如何讓殖民地的自然狀況、工業產品和發展需要滿足帝國主義的剝削需求。英帝國晚期的這種“發展型帝國主義”,與美國“馬歇爾計劃”所代表的“發展現實主義”對外戰略,以及聯合國的技術援助計劃同步展開,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盡管英帝國針對北美、大洋洲、亞洲、非洲、拉美等不同殖民地的發展理念不同,但這種以科學研究為先導,通過“多出政策、少出錢”的有限干預,緩步刺激經濟發展的模式,本質上是將發展置於自生自發、自由放任、自由競爭的經濟學假設之下,旨在將以英國經驗為樣板的現代化模式推廣到整個帝國。
事實上,這也是美帝國崛起之後,英帝國航船不得已的姿態調整,英國不得不從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變成新興超級大國的小夥伴,不得不借助英美同盟和“殘余帝國”勢力範圍來發揮國際影響力,不得不借助美國遏制共產主義的戰略來保留海外基地,不得不與美國彼此分享情報。英帝國這個曾經的“世界島”,讓位於美帝國這個“大陸島”。
美國以西方世界主導者的姿態,全面取代並填補了英帝國收縮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和科學真空。核武器技術、尖端武器技術和信息技術等科學進展,讓美帝國擁有了戰略威懾能力,監控全球信息流動的能力,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軍事能力,對日本、韓國、德國和北約軍事指揮權的絕對控制權,加上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讓美帝國借助不對稱的軍事優勢得以鞏固下來。
美國由此成為發展話語迭代的主要推動者。如果說英帝國時代的發展話語以經濟為主軸,那麽美帝國時代的發展話語的重心就在於政治。美帝國的發展話語,以政治發展為主,以經濟發展為輔。
換言之,在美帝國的發展話語中,經濟發展總是以政治發展為條件,相比於經濟財富的集中與分散,美國更關心發展援助對象政治權力的分散與集中。
與英帝國主導的發展話語1.0時代不同,在美帝國主導的發展話語2.0時代,美國社會科學的崛起是關鍵要素,它重塑了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方式,形成了美國主導的發展理念,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國家之間的話語競爭。在此過程中,美國長期以來的私立精英大學體制、商業利益集團設立的各種私人基金會以及美國政府,成為最重要的三大行動者,三者之間的關係從松散的合作轉向緊密的融合,最終形成旋轉門式的制度化互動模式。
在進步時代三者的松散合作關係中,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等私人基金會資助了包括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美國學會理事會、美國地理學會、太平洋關係研究所、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和國際非洲語言和文化研究所等大量研究機構,後者所形成的國際科學網絡,用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將非西方社會置於需要用生發於西方世界的現代價值觀來改造的前現代落後境地,而改變這些社會的前現代狀況意味著美國影響力的穩步提升。
在大蕭條直至冷戰初期,三者之間形成了影響至今的戰時團結紐帶。“二戰”期間,私人基金會和美國政府都意識到美國將在戰後繼承或重組過去由歐洲主導的世界事務,這需要建立全新的研究體系來生產所需要的新知識,繼承或重組整個世界。美國戰略情報局打破了情報的傳統定義,將對全球每個民族和地區的了解都視為情報問題,因此邀請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美國學會理事會集合了數百名年輕學者和資深學者擔任情報專家,他們建立了新的分類標準,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納入統一的排序體系和話語體系,並著手全面重組美國的教育機制,來生產帝國所需要的專業知識。
20世紀50年代,冷戰升溫,三者之間的關係也隨之升溫,形成了旋轉門式的制度化互動模式,區域研究成為美帝國的戰略顯學。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建立了針對斯拉夫、拉丁美洲、近東中東、當代中國、非洲、日本、韓國、東歐、南亞、西歐和東南亞在內11個區域研究委員會,福特基金會在美國34所著名大學建立了具有高級學位授予權的跨學科區域研究所,推動區域研究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1957年,蘇聯率先發射了人類社會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號,徹底擊潰了美國國內對政府資助區域研究的反對意見。美國政府於次年通過《國防教育法》,為美國各個區域研究機構提供大量資金,並於1961年極大地擴展了1946年設立的富布賴特項目。福特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合作,將過去相對獨立的學術界和政府聯合起來,建立了新的專業知識網絡,改變了美國社會科學的面貌,培養了冷戰時代最有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他們的研究成果定義了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和前沿。其中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比較政治分會的政治發展研究叢書,以及著名經濟學家沃爾特·羅斯托的《經濟增長的階段》,等等。
無論是1.0時代還是2.0時代,英美帝國主導的發展話語都將科學作為帝國文化霸權的基礎,自然也都不乏批判之聲。比如,今天被視為客觀普適的科學認知方法,其初衷是為了歐洲人理解並佔有殖民地的領土和人口資源。20世紀70年代的依附理論就主張科學不是發展的關鍵,因為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依附關係很難打破,即使是在殖民帝國土崩瓦解之後。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學家加強了這一觀念,他們認為科學的直線擴散和線性的現代化理論,或許更容易在澳大利亞這樣的白人殖民地實現,在熱帶非洲卻很難實現,因為歐洲人總是處心積慮地防止被殖民者獲得科學知識,目的就是為了將熱帶非洲的經濟發展永遠置於西方的支配之下。
概言之,英帝國與美帝國所主導的發展話語變遷,與作為帝國文化霸權的科學敘事息息相關。英帝國的殖民地大多在熱帶,因此也被稱為熱帶帝國。但對英帝國而言,熱帶並不是一個氣候概念,它首先是一個環境概念,那裡有自己的疾病、作物和自然法則。它又是一個種族概念,那裡布滿了未開化的、蒙昧的黑人。它也是一個性別概念,歐洲人是男人,熱帶人是女人。它還是一個醫學概念,那裡是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危險地帶。它還是一個發展概念,那裡需要西方人在物質上、社會上、經濟上指引其發展。熱帶的一切都不成熟,只有財富是現成的,等待宗主國去收割。對美帝國而言,經濟和社會的不發達,都是因為政治的不現代,發展的理念、道路和目標都必須以發達的美國模式為標準。很顯然,對於這個在過去30余年中形成的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而言,“經濟學帝國主義”是一種具有高度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和意識形態,籠罩著人文與社會科學,它們和自然科學一道,支撐著美帝國的文化霸權,推動著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這一帝國發展話語走向世界。因此,對於美國與世界而言,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話語都既是一種政治文化,也是一種文化政治。
四、結語:發展議程的“去殖民化”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科學與帝國之間關係的三種敘事發展到今天,可以統稱為北大西洋的故事。北大西洋的故事形成始於18世紀中期。在此之前,北大西洋還沒有進入歐洲人的思想世界,只是“埃塞俄比亞海”“北海”抑或“西大洋”。18世紀中期以來,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歐洲人之間包括奴隸貿易、商品貿易在內的三角互動,改變了每個大陸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讓北大西洋成為一個分析單位。到了19世紀末,歐洲人形成了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北大西洋偽科學概念。在虛構的彼此和睦的種族關係和血緣關係中,從東到西,歐洲新教徒及其美洲後裔、南方人、非洲人以及猶太人,構成了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建立了所謂跨大西洋團結機制。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所以沒有和華約組織一道解散,不僅僅是強者的傲慢,也意味著美歐聯盟所支撐的北大西洋世界帝國夢想仍未破滅。
這個世界帝國夢想推動了北大西洋標準的全球化。詹姆斯·斯科特設想了這樣一個未來場景:來自北大西洋的商人,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走下飛機,迎接他們的都是一套熟悉的東西,從法律、商業、交通到物權、土地所有制和監管,都來自他們的故鄉,只有食物、音樂、舞蹈和服飾保留了異國風俗特色,但即使是它們也完全成了商品。這是因為,18世紀中期以來,北大西洋崛起的現代民族國家,憑借其基於科學的文化與政治霸權,以普世制度的名義大行其道,殖民帝國競爭和現代化發展競賽推動了這套制度的普及,並在1989年之後從兩個方向變成了一套單一的標準,意欲征服全世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法庭等國際組織,也都致力於在全世界範圍內推行標準化的最佳實踐,這些標準也來自北大西洋國家。
從文明使命的載體到支配控制的工具,再到文明的控制或曰文化霸權,科學與帝國的興起亦步亦趨,科學與帝國的擴張密不可分。晚近30余年來,米歇爾·福柯和愛德華·薩義德的思想深刻影響了殖民帝國的科學研究和對西方化的現代化的反思,布魯諾·拉圖爾將科學視為宗主國對殖民地本土知識進行轉譯的產物,為反思發展話語的變遷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發展中國家的學術界興起了本土化浪潮,希望反思源於歐洲的主流科學,彰顯本土文化的自主性及其對歐洲科學的影響,探尋自身的現代性。對於意欲追求自主發展道路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要想開啟發展議程的“去殖民化”進程,有必要重新理解科學與帝國的關係史,深刻反思北大西洋標準的全球化,進而厘清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將現代化與西方化區分開,找到真正符合自身傳統、文化和人民需要的發展道路,譜寫行穩致遠的發展篇章。
(本文原發於《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