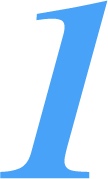豐子恺的詩化教育
時間:2022-01-06 歷史與文化
豐子恺先生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他有六個孩子,又領養了甥女豐寧馨,七個子女以及第三代、第四代都很出色。其中有些孩子,某個教育階段沒有去學堂,而是由豐先生親自在家授課,類似私塾教育。
在所有的科目中,豐子恺特別重視詩化教育,從小培養孩子對古典詩詞的興趣,為他們打下了扎實的文學基礎。從海豚出版社的上中下三冊《子恺書信》可窺知一二。最小的女兒豐一吟一直和父母同住,沒必要寫信;幺兒豐新枚1959年離開上海到天津讀大學,1964年他從天津大學畢業後,回上海進修兩年,1966年文革開始,豐子恺被批,新枚未能留在上海,被分配到石家莊,豐子恺給新枚的信當然就最多了。在給新枚的信中,幾次提到馬一浮的詩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憶六橋。”當時,馬一浮在蜀,回憶杭州西湖,不用典,只白描,豐子恺稱贊馬一浮寫得好。馬一浮回杭州後住西湖蔣莊(六橋),1967年去世。豐子恺一再感慨“可惜遲死了一年”,1966年文革爆發,馬一浮被逐出蔣莊,第二年死在城中陋屋內,若早死一年,落得乾淨。
在給幺兒的信中,經常玩詩歌集句遊戲,“一”字起頭的、“三”字開頭的,等等。豐子恺還摘抄一些有趣的故事給兒子看,譬如《兩般秋雨盦隨筆》裡的一則:父給子五千金,讓子去京應試,子不考,卻尋花問柳,得病而歸。父檢其行囊,見詩稿有“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之句,父大贊,曰:“足值五千金。”
豐子恺告訴新枚:“我近常默背古詩十九首,這無名氏作品,實在很好,可謂五言詩之鼻祖。”可能因為是私信,可以談一些不便公開的觀點,譬如:豐子恺認為蘇詞不夠細膩,只能高喊“大江東去”。隔一天,他又寫信給新枚修正自己的看法:“我前信批評蘇東坡,說他只能高叫‘大江東去’,不宜描寫細致景物。此言太過了。”雖然,做了糾正,但豐子恺對蘇東坡可能還是抱有偏見。豐先生對杜甫也有不同看法,他對新枚寫道:“來信提及《秋興八首》,我嫌其太工巧,少有靈性表現。”這個觀點,也會有爭議,但有獨特見解總比人云亦云好。
豐子恺也善於觀察生活中的詩意,鄉下的風是“橄榄風”,兩頭小,中間大,即晨夕小,中午大。豐先生寫道:“ ‘橄榄風’,我對‘黃梅雨’,不很妥。唐雲對‘芭蕉雨’,太文雅,非俗語。”看到剃頭店的對聯:“頻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豐子恺甚贊此聯對得好,彈冠相慶是得意,搔首問天是失意,來的都是得意人,理完發,走出店,也沒有一個失意人。

古詩詞也常入豐子恺的漫畫。1971年8月11日,他在給新枚的信中曰:“讀辛稼軒詞,發見一畫‘西風梨棗山園’。可入‘敝帚’中,成六十四幅。”《敝帚自珍》,是豐子恺最後一本畫集。辛棄疾《清平樂·檢校山園書所見》下阕如下:“西風梨棗山園,兒童偷把長竿。莫遣旁人驚去,老夫靜處閑看。”這幾句詞很有畫面感,又有童趣,很適合豐畫。
在給弟子潘文彥信裡寫道:“詞這種文藝格式,世間只有中國人擅長。日本人模仿漢詩,但不解詞。”詞乃詩之變格,言情更為細致纏綿。豐子恺很喜歡《白香詞譜箋》,書信裡時有提到。清朝舒夢蘭(字白香)輯《白香詞譜》,流傳極廣,被稱為“詞學入門第一書”。後謝朝徵加以箋注,成《白香詞譜箋》。豐子恺曰:“我近讀《白香詞譜》,愛其‘箋’。箋中有許多可愛的作品。”
潘文彥曾在文章裡提及:“新枚的指導老師胡炳堃,畢業於復旦英語系,是我熟朋友。我常去他家玩,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認識豐子恺先生,他的兒子豐新枚,現在在我那裡學英語,成績很好。特別是他的古詩詞,我們老師中,沒有一個及得上他。’ ”

豐子恺有一張畫《日月樓中日月長》,上面題詞曰:“余閑居滬上日月樓,常與女一吟、子新枚共事讀書譯作。寫其景,遙寄星島廣洽上人,用代魚雁云爾。”落款是:戊戌子恺。戊戌年是1958年,畫面上三人皆穿灰色布衣,圍桌讀寫,氣氛祥和,桌子上一爐袅袅香火煙,更是平添意趣。書香世家子弟就是這麽“薰”出來的吧?小女豐一吟繼承父親衣缽,善畫“豐家樣”漫畫,為世人所知。他最小的孩子是豐新枚,也即畫面上中間那位。中國傳統父母格外疼愛“老幺”,所謂“最小偏憐”。1938年,新枚在桂林出生,豐先生一家當時在逃難中,40歲再得一子,也算是流離生活中的一樁喜事。他經常戲呼新枚是“抗戰兒子”。
豐家子女很幸運,有這樣一個喜好詩詞和藝術的父親,並得其教化。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