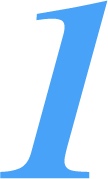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遭逐”兩年後空降中時,難逃“被害”命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三)
時間:2019-07-30 歷史與文化
(在我抵達紐約正式報到的前半年裡,就曾四次奉召從匹兹堡飛到紐約和余先生開會,参與了《美洲中國時報》全部的籌備過程。圖為我(右)和余先生在匹茲堡大學前留影。作者供圖)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三。
---------------------------------
以一句話來區別王惕吾和余紀忠兩位報老闆在美辦報的差異,就是——王老闆主要是辦給支持國民黨的人看的,余紀忠則是希望不支持甚至反對國民黨的人也願意看。不論余先生是如何絞着腦子想出來十四字箴言(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又如何百轉千回說出來,所透露的辦報哲學無非是想幾面兼顧,多方爭取。
有這個思慮辦報自然就多了風險,自然就要多傷腦筋,就必然在用人上見心思。
首先,余先生敦請黨國大老級的陳裕清先生擔任總主筆。陳裕清先生受業於美國名校,並受知於蔣介石,長年負責國民黨的文宣和海外組織工作。他也是一位老報人,思想開明,謙和儒雅,是余先生少數敬重又合得來的黨國人士。請他主持筆政,有向黨内輸誠的宣示意義;同時也不會在余的統籌全局中形成掣肘。
除了陳裕清先生,余先生還晉用了不少在海外兼有黨務身份的留學生,不過多半把他們放在業務部門,借助他們的幹練和人脈關係拓展廣告發行業務。相對地,有不少不具黨工背景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生任職紐約總部,是編譯部門的主力。理所當然,余先生還爭取了幾位原在新聞局駐外單位工作的人,甚而曾在黨報工作的人。這些人所謂“根正苗紅”的出身背景,都有助於向有關方面釋疑:余紀忠不僅不會與黨國疏離,反而結合並重視黨國人才。
此外,他從台北總社挑選了一批年輕新秀,也召集了好些正在海外就學或行將學成的子弟兵,以及就地取材,邀聘經年在美就學就業的優質青年。他們具備一定的語文條件,組建成了負責採訪與涉外等實務工作的核心隊伍。
這個囊括了各方菁英的組合,除少數來自香港,其餘都是台灣培養的人才,他們知識程度高,見識廣,有基本的獨立判斷能力。在意識傾向上,左中右獨無所不包,但並沒有顯見甘受意識形態捆綁的人。總的來說,中間及中間偏右的居多,也多能服膺余紀忠的辦報理念,亟盼一份有別於《世界日報》的華文報誕生。當時的参與者後來不論回到原鄉或是留在異鄉,都算得上頭角崢嶸,能在台灣和香港不同的媒體形態中“呼風喚雨”。
就記憶所及,曾在《美洲中時》任職較為知名的人士大抵有:(美東)黃肇松、林博文、傅建中、龔選舞、胡鴻仁、詹宏志、邱立本、徐啟智、傅崑成、譚立信、辜尚志、金惟純、楊人凱、蕭嘉慶、鄭漢良、CoCo、梁章通、杜念中、周陽山、邵宗海、陳一新、范疇、楊澤、陳玉慧、馮光遠、羅文輝、李傳偉、王幼波、張靜濤、梁東屏、袁家松、先嘉源、冉亮、羅鴻進、黃志鵬、傅易易、邱秀文、郭貞、何清。(美西)趙怡、彭中原、卜大中、周天瑋、林添貴、陳亮月、鮮正台、溫禾、林麗蓮、林馨琴、吳忠國、陳子巖、陳萬達、張靖宇、江啟光、趙健、張晶、莊安理、陸炳武、強偉城。(台北)南方朔、孫思照、李彪、陳文茜、陳守國、夏迪、劉克襄。(香港)江素惠。(日本)秦鳳棲、劉黎兒……。
在《美洲中時》航向新大陸不久之前,事實上已有一份報紙捷足先登,并且另一份報紙也正要開張。前者是當過立法委員的高雄眼科名醫、台灣時報老闆吳基福,1980年在舊金山辦的《遠東時報》。後者是曾為閻錫山麾下、當過律師的《台灣日報》老闆傅朝樞,確定要在紐約辦的《中報》。
《遠東時報》不堪賠累,1982年5月停刊。而傅挾國防部總政戰部收購《台灣日報》之資,並全數結匯其在台資產,約五億新台幣,於1982年2月27日在紐約發刊《中報》。
(《台灣時報》為台灣的綜合性日報,創立於1971年8月25日,吳基福為首任董事長,舊總社位於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0號)
吳基福從台灣帶來兩位媒體前輩主持編務、筆政,他們都比我年長十幾二十歲,二人因個性、觀念並不盡同,相處得很勉强,其中之一在《遠東時報》倒閉前即已被傅朝樞召為《中報》總編輯。
《遠東時報》延續《台灣日報》傾向黨外的風格,早一步顯示了黨外本質上的親台獨意味。《中報》不見容於蔣經國被趕出台灣,先在香港創辦,繼而延伸來美,已藏不住親中媚共的傾向。
以余紀忠的個性,聼聞這兩位已先在美登陸的媒體人,一定是不會放過,必要網羅到手的。余先生對我說,要借當年他們在台灣辦《台灣日報》成功的經驗,及後來在美國辦《遠東時報》失敗的經驗。同時,把傅朝樞的主將挖過來,也可削弱潛在敵人的力量,減少對《美洲中時》的威脅;並經由他或可管束對國民黨的傷害。這是余先生津津樂道的戰略思考。
余紀忠如願以償,兩人先後來到《美洲中時》,一個在創刊前,一個在創刊後。(我)猶憶後者的來到使前者臉色大變,因余紀忠未與他商量,亦非經他洽談,倒是余還命我做過中人。旋即,前者明升暗降,轉任社長,後者取而代之。《美洲中時》創刊後八個月,總編輯就換了人。
從人事結構上看,大抵是個兼容並蓄之局。余紀忠基本能顧到國内的看法,但在總編輯這個角色上,顯然較看重有過衝撞體制經驗的人,並且敢大膽啟用背景不深,卻具戰略價值的人。余紀忠藉着用這樣的人表達進步性,相對於陳裕清,是另一方面的宣示意義,並自信他的個人魅力足以駕馭。先別說能不能駕馭得住,光這個路數就夠人議論個好一陣子。
不過,這麼一大攤子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聚攏在一個需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地方,打拼一張辦得再好都不易賺錢的報紙,乃是一樁極其艱鉅的工程。自古文人相輕,多屬自戀,首先磨合就不容易。
以紐約總部為例,被換下來的總編輯是個並不具人格魅力的老派文人,很快就使人覺其言語乏味、心胸狹隘,即便有過在美辦報經驗,卻不覺其有所準備而見高明。這兩類人特別與他不合:過去和他工作過和在台北跟過余紀忠的子弟兵。前者礙於情面不好明杠,私下議論卻源源不斷。後者不時酸語相向,甚至明面上抵制,常迫我做些無效的排解。在余紀忠與他的“蜜月階段”,台北子弟沒佔到便宜,要不瞻顧不前,就是遠走美西,再不辭職就學,因而受到折損。
總之氣壓很低,一位頗具觀察力的老兄形容得妙,《美洲中時》創刊伊始,“士無鬥志,將有降心”,言罷大笑三聲,聞者無不絕倒。縱使所述不免稍嫌誇張,倒也予人詭異中入木三分之感。
接下來該說說我自己了。
許多人熟知我是《美洲中時》總編輯,其實我是第三任,而掛上這個職稱連前帶後不過六個月零11天。之所以會令人印象如此深刻,是因為從第一天開始,我的付出和最後報紙停刊的“周天瑞因素”——我的承擔,充滿了血汗和血淚,使我與這份報紙彷彿有着生與死的關係。
話說在我抵達紐約,正式報到的前半年裡,就曾四次奉召從匹兹堡飛到紐約和余先生開會,参與了全部的籌備過程,應該最清楚他的想法。但是開報當時我只是採訪主任,起初甚至連副總編輯的頭銜都沒有。兩年前我從台北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掛了三年副總編輯銜,如今歷練更多,又唸了一個學位,卻安我一個採訪主任,豈不情何以堪?
非也,我不但沒有一點不高興,而且欣然接受。這有幾個原因:
一、1980年6月,余先生命我閃電赴美,其實有着加強磨練的意思,因為在蒙他不次拔擢的過往三年半當中,彼此之間因新聞處理頗多齟齬,他很傷腦筋;我自己也多次求去美。他藉着情治單位對我的“關切”和“注意”,送我出國,固是讓我避禍,實則很多人看來是放逐。在“遭逐”兩年後,因余先生創報而獲徵召,意味了重新面對余老闆,也意味著彼此要重新合作。他既要驗收磨練成果,我也要看看是否繼續追隨他,所以職務低一點最好。
二、余紀忠以極端重視人才聞名,新創報紙使他在用人方面“大展拳脚”,特别對於一些已具名號的人,他若不納入囊中便難安枕席。報紙的發行人、社長、總編輯、總主筆這類主要頭銜,他自要虛位以待,好招賢納才,以示海納百川。何况,我在余氏門下已逾載,堪稱子弟兵、自家人了。先擺在一邊見習見習,不擔太大的責任,倒也挺好。
三、既是新創事業,就是重啟爐灶,在新天新地用新的觀念、新的心情看待一切,自應擺脱舊包袱,適應新環境,接納新伙伴。海外辦報從零開始,花費大而進帳少,工作條件全都不能與國内相比,當時坐鎮台北為美國提供大量後勤製作版面的王杏慶(南方朔)曾標舉“勤儉辦報”四個字,最能反映這樣的心境。文窮而後工,每個人都該艱苦以對,哪能計較職稱、名位、待遇?唯有做出成績,經得起考驗,才是硬道理。從低階開始是好的。
我乃以全新的心態,甚至以自己創業的心態面對新事業。我固已不是新聞界的菜鳥,畢竟在美國辦報還是頭一遭,當然首先要虛心。這不是故唱高調,其實是合乎現實的,為了立足新土,為了生存,必須虛心!
所以,開報當時和之後走馬換將,都沒讓我擔任總編輯,我真的並不在意,還正樂得認真去想該怎麼辦好這份報紙。
不過由於是老幹部,又是從台北來美最老的一個,因此余先生凡事習慣找我,被交付的大小任務多如牛毛,可謂“族繁不及備載”。諸如,老闆想要延攬的人,往往要我幫忙先接觸、試探、遊說;陸續晉用的編、採、譯、校,幾由我面談後報給他;他在各地的跨部門、跨地區會議,未必召社長、總編輯,卻必召我參加;至於經常有的改版、協調、檢討,更是之前擬計畫,之後寫報告,無役不與。為了這些事,不時要在各地出差,境内境外到處飛,非常忙碌。
這樣好嗎?當然不好。余先生覺得方便,就便宜行事,但在我與我的長官之間便創造了矛盾,無論我如何“行禮如儀”,都難消戒心。被看成是余紀忠的監軍,是極自然不過的事。為此我在工作和處境上不平靜,也是必然。
我卻不願以監軍自命,這不是我喜歡做的事,追隨了多少年,余老闆很難聽到我議論我沒有考評權的人。何况這些外來的長官都是年齡、資歷長我許多的文化人,文人可以相輕,絕不可以相煎!否則被人說成是嫉賢妒才、陷害忠良的東廠小人,可不是我要博的名聲。
不過,余紀忠不會從這邊聽到那邊的,絕不表示不會從那邊聽到這邊的。
這很正常,大凡跟余先生工作的人,不管年紀大小、職務高低,都想邀他重視。在台北那些年,我經歷了、也看了很多。眼前這些新來的前輩,若有安全感危機,就必格外要刷存在感。刷存在感最簡便的方法,自然而必然地就是在我身上做文章。於是自然而必然地老闆會公開駡駡我,自然而必然地會明顯疏遠我;也自然而必然地氣氛會變得緊張,自然而必然地影響我的心情。
這是我無法逃避的命運。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70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刊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
【延伸閲讀】
中時遭暗算,報人余先生要把自己送出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二)| 周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