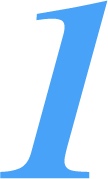德先生離不開賽先生
時間:2019-11-06 歷史與文化
雖然已經到了年末,但是現在還是2019年,亦即仍在五四一百周年的範圍之內。所以,今天來談一談五四諸賢當年引進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應該還算是應時應景吧。
在鋪開來談之前,或許還得先科一下普,掃一下盲,介紹一下這兩位“先生”到底是誰。畢竟現在有些地方的“去中國化”之風刮得很猛,在那種教育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尤其是零零後,沒准還真不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身份。

孩子們,聽好了!“德先生”的全名是德莫克拉西,“賽先生”的全名是賽因思。這兩兄弟都是五四那年頭從西方漂洋過海過來的舶來品,所以他們的外文名字Democracy和Science都得音譯成漢語,中國人才能聽得懂,讀得來。
上面既然說到應時應景,現在就順便解釋一下。應時是因為現在是五四一百周年,聊聊這個話題有紀念意義。至於說應景,大家只要看一下世界各地層出不窮的“民主鬧劇”,不用腦袋想也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
中國人可能不知道,打從五四以來大家都一直十分重視,不僅經常同時掛在嘴邊,也會落到實處的民主和科學,在他們的西方誕生地,其實並沒有多大的血緣關係。即便是有,那也是在五服之外,幾可忽略不計。
五四諸賢當年之所以在從西方引進的種種新概念裡頭,格外鍾情民主和科學,那是因為這是那時的中國精神市場最缺的兩種緊俏貨。引進民主,是為了打倒專制;引進科學,則是為了破除迷信。而在西方,民主是民主,科學是科學,分屬不同領域,幾乎沒有人會把它們相提並論。
換言之,五四以來的幾代中國人在接受民主政治理念的教育時,也接受了科學實證精神的訓練。而在這兩者之間,中國人更加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因為科學可以實證,比相對而言概念化得多的民主,要更經得起考驗,也靠譜得多。
所以,當西方人(此處指廣義的西方人,包括當年的蘇聯人)向中國人硬銷形形色色的各種民主制度,尤其是近些年來鋒芒畢露的美式民主時,中國人卻從科學的實證精神出發,認為西方制度不一定適合中國的國情,迷信西式民主,生搬硬套只會產生淮橘為枳的惡果,所以打從1949年建國那一會開始,中國人就是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來量身定做典章制度。甭說中國人獨創的政協制度,即便是人大制度,也不完全是蘇維埃的翻版。

(具有歷史標誌意義的小崗村“包產到戶”紅手印契約)
不久前,筆者看了一部叫做《黃土高天》的電視劇,劇中的一段劇情令人深受啟發。當時,劇中的青年農民秦學安所在的那個大隊的村民正在進行基層民主投票,以決定是否要接受“包幹到戶,包產到戶”的改制。就像所有的民主選舉一樣,在這個過程裡,主張改制和反對改制的村幹部都發表了意見,最後交由村民來投票決定。村民們後來決定接受改制,而且並不是懵懵懂懂地投票,而是在掌握了充分資訊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才做出的選擇。
首先,秦學安是在安徽看到“大包幹”的成效後,才動了回陝西老家推廣安徽經驗的心思。回到家後,他也是先在自己領導的二大隊試點改革,初見成效後再試圖說服村領導和其他村民。到了後來,更是在有了中央文件的撐腰後,才舉行村民投票的。
這樣的民主顯然是科學的,因為村民是在掌握資訊,充分知情的情況下,才行使的民主權利,結果自然能促進經濟生產和社會發展,是優質民主的體現。反之,如果村民既不充分掌握資訊,也不瞭解實際情況,卻要他們投票做出決定,他們只能根據持不同觀點的村幹部的講話來判斷了。比如說,這個大隊的村民根本不知道安徽的改制經驗,也沒有人在大隊裡搞過試點改革,而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繼續學大寨”和“學習小崗村”這兩個選項,那他們會做出什麼選擇呢?一般情況下,在發表意見的村幹部中,誰的勢力更大,誰能給出更多好處,誰的話語更具說服力,誰長得更帥等等,就會成為村民投票時的優先考量。而最關鍵的問題,哪一種制度會對自己和整個大隊的發展更加有利,恰恰就不在其考慮範圍內。
當代西方社會的民主困境,問題就出在德先生缺了賽先生的規範與指導。讓選民根據各個候選人的競選綱領做出選擇,就像讓消費者根據同類產品的不同廣告來選購產品一樣,風險極高。
在筆者看來,比起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普選民主,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恐怕要來得靠譜得多。
(作者是新加坡華人,前資深媒體人,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