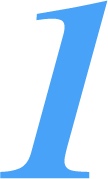淪落天涯的主僕
時間:2020-06-19 歷史與文化
中華民國甫成立,臨時大總統孫文曾對一人有過如下的評價:“武昌起義,山西首先回應,共和成立,須首推山西閻都督之力為最。閻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此處的“閻都督”“閻百川”,即統理山西38載,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
閻錫山字百川、伯川,早年參加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參與推翻滿清、創立民國,後參加中原大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在1949年6月13日,任風雨飄搖的蔣介石政權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不及半載,便於1949年12月8日敗退台灣,1950年3月16日卸任“行政院長”等實職,轉任“總統府資政”虛職,卜居陽明山,至1960年5月24日病逝,享年76歲。
閻錫山早已走進歷史,對他各個方面的評價,也已蓋棺定論,毋庸贅述。閻錫山之所以引起我的關注,起因並非其本人,而是他當年的隨扈張日明先生。網上轉載2010年1月7日《聯合報》的一條資訊,一位名叫張日明的山西人,從15歲起就跟隨閻錫山到處征戰,後追隨閻到了台灣。閻錫山到台不久即在政壇失勢,張日明的軍旅生涯宣告結束,連一毛錢的退撫金都沒拿到。因感念閻錫山對桑梓曾經有過的貢獻和對自己的恩遇,閻辭世後,張日明在近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裡每日搭公車上山,為閻上香,掃墓,成為忠誠的守墓人。張日明的忠義之舉通過網絡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
從網上搜到閻錫山的種能洞在陽明山,我便利用來台灣休假之機搭公車上陽明山。但問公車司機,閻錫山故居、墓葬所在,不知;問同車乘客,竟無人知曉閻錫山這個名字。我深感詫異。無奈,只得在中山樓那站下車,慢慢沿路尋訪。行人甚少,空載的計程車也不多,邊走邊問,餓了便走進路邊餐館點一碗牛肉麵充饑,這樣走走停停近兩個鐘頭,直到走到永公橋那個地方也未尋獲種能洞的確切地址。正當我無計可施,幾乎就要放棄之時,一輛計程車戛然停在了我的面前。司機是一位63歲的黃先生,曾經當過導遊,對閻錫山等歷史名人十分了解,說起他們的掌故來,如數家珍。於是我便搭他的車來到士林區永公路245巷34弄的閻錫山故居種能洞和不遠處的墓園。

種能洞和墓園均藏身榛莽,十分偏僻,據說種能洞初建的幾年,無水無電,交通不便,蔣介石夫婦兩次蒞訪,閻錫山親自指揮僕役墊磚修路。而今種能洞故居和墓園雖已被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跡,但財政撥款捉襟見肘,處處顯露出破敗的景象。故居的屋頂和墓園的斜坡上都用水泥砌出一個大大的“中”字,十分搶眼。據說,砌“中”字,所依據的是閻錫山秉持的處世、為人、為政,都要“發於仁,歸於中”的思想哲學。閻錫山認為“宇宙本體是中,中是不偏、不過、不不及”。
張日明先生不在此處,講解員說張日明先生自己也年屆米壽,現已不能來閻錫山故居和墓園打理,每日在其石牌的住家過活,頤養天年。黃司機說張日明先生家他也去過,於是我又乘黃司機的車到了實踐街85號張日明老人家中。老人雖已88歲,行走不便,但思維清晰,一張口便是濃重的山西腔,聽來十分親切。張老說他近些年來無法上山為老長官上香、掃墓,只好改由妻子和兒女代他來做。我給眼前這位忠厚的老人講故鄉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混濁的眼睛中頓時放出光彩;我又問他這70年來是否回過山西老家,他馬上垂下眼簾,眼神暗淡下去。我的眼睛濕潤了,趕緊按家鄉的習俗將一點心意塞在這位生活顯得拮据的老人的手心裡。

(張日明坐在閻錫山墓園台階旁。圖片來源:中央社)
走出張日明老人的家,回望被夕陽染成金黃色的陽明山,眼前又頓現閻錫山故居和墓園裡大大的“中”字。那“中”字固可解作“中庸”之意,但不是更可以解作“中國”之“中”嗎?閻錫山來台的10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後10年,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他的故國——中國。張日明老人辭別故土70年,他為老長官義務守墓近60載,某種意義上說,他所守護的或已不是一座墳塋,而是對故國的一份深深的懷念、眷戀之情,他所秉持的不也正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骨子裡都有的傳統的忠孝仁義觀嗎?
(作者是澳門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