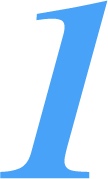張愛玲筆誤再探:失落的1945
時間:2020-12-10 歷史與文化

《對照記》“圖五十”是一幅1955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去美國前的照片,妝容精致側臉垂目。張愛玲記述從香港乘船途經檀香山,海關關員是個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寫:身高六呎六吋半,體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五呎六吋半寫成六呎六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弗洛依德式的錯誤)。“心理分析宗師弗洛依德認為世上沒有筆誤或是偶爾說錯一個字的事,都是本來心裡就是這樣想,無意中透露的。我瘦,看著特別高。那是這海關職員怵目驚心的記錄。”
《對照記》“圖四十一”,張愛玲“粗心大意”誤記為“1943年”的那幀與李香蘭合影,被學者認為是她上海時期最重要的照片。港大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教授有一篇論文《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其分析就從這照片開始。攝於1945年7月21日,距二戰終結和日本投降僅僅三周,“這張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將當年兩位最耀眼的女性文化形象放在了同一個框架中。它的奇特構圖及不甚協調的視覺風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識照片背景的觀者甚至將它視為一個描繪日本帝國崩毀前夕,日中組合搖搖欲墜的視覺寓言。”
1945年7月的李香蘭和張愛玲都已赫赫有名,同為上海淪陷區文化人代表。張愛玲後來輕描淡寫的納涼會——“園遊會”,在當時所有媒體報道中,皆被描述成一個“眾星雲集”的場合。出席者除了李香蘭、張愛玲兩大紅人,還有媒體巨頭:申報社社長陳彬龢,後台是日本;平報社社長金雄白,以周佛海為靠山;日本殖民高官松本大尉、中華電影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也在座。黃心村的質疑切中要害:當地傳媒何以對日本即將落敗的蛛絲馬跡如此無感,在帝國崩壞前夕,仍大張旗鼓為那場盛會錦上添花?
黃教授對照片的分析,圍繞張愛玲和李香蘭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蹺構圖,兩人迥異的裝扮風格,尤其是張愛玲乖張的坐姿,偏離鏡頭的朝下視線,種種細節,抽絲剝繭。她說:“張愛玲的臉部表情和身體,或許暗示著抗拒抑或是蔑視,但更重要的是,她顯然懂得將攝影鏡頭對她的凝視,反轉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興趣的是,對媒體“無感”的犀利質疑,不也同樣適用於這些出席者:張愛玲、姑姑、炎櫻,在日本戰敗的三周前,是抱著怎樣的心情赴此“中日聯誼盛會”?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局驟變,身為汪政府要員的胡蘭成遭國民政府通緝倉皇逃亡,又如何給張愛玲帶來震驚惶恐?
忽然想到應該重溫《小團圓》。1945長長的夏天發生了什麽,書裡都有敘述。而且,第八章開頭,張愛玲寫九莉的那些話,簡直就是對後來自己那個“筆誤”的註解:“從這時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內心有一種混亂,上面一層白蠟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靜安全感。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總當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這一年內一件事也不記得,可以稱為失落的一年。”
“她剛認識他的時候就知道戰後他要逃亡,事到臨頭反而糊塗起來,也是因為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裡擯除了1945。
“或許張愛玲自己也不願意相信,這照片竟拍攝於日本戰敗前夕。”黃心村寫在論文“註釋”裡的一句話讓人心顫。是的,沒有1945,只有1943,只有上一年或下一年。雖然《對照記》問世的1994年,離那段不堪和混亂的日子已有半世紀之久,而她也依然記得,有一種叫作弗洛伊德式的錯誤。
關於記憶和遺忘,心理學有很多說法。張愛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記憶,是因大腦海馬體損傷造成逆行性失憶,還是情緒性記憶的主動遺忘?至此已不是問題。當然,探討其間隱秘非為“祛魅”,如黃心村所言,只為“還原一個歷史的張愛玲”“更複雜的張愛玲”。
下意識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刪除記憶晶片上的黑暗塊面,我們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嘗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這樣的說法:最終構成人一生的東西,不是閱歷、靈性與任何事件,而是對所有這些經驗的記憶、描繪和闡釋。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廟的鐘聲/停了,但花中余音/持續地回響。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