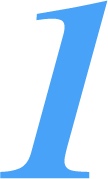爸爸的白粽子
時間:2019-06-06 歷史與文化

中國的傳統節日伴隨著味道,不需要看黃曆,走在巷弄,蒸騰的粽葉香撲鼻,就知道端午節來了。
媽媽是台灣彰化縣人,為了爸爸,學了一手江浙菜。媽媽是家中最小的女兒,燒菜輪不到她,幫嫂嫂們帶孩子,年紀輕輕學裁縫掙錢,才是她的工作。嫁了懂得吃、愛吃的江蘇爸爸,家裡又總是同事、親朋好友、部隊袍澤來打牌蹭飯,總得學幾招。爸爸是教媽媽做菜的第一個師傅,再來就是“外省媽媽”環伺的鄰居們,教了媽媽好幾道大江南北的外省菜。
我家的飲食習慣是“父親至上”,爸不愛吃的,媽媽鮮少端上餐桌。口味走的是“外省風”,粽子就是一個例子。上小學前,我以為鹹粽子就該是長型的、裡面一塊五花肉,有的有鹹蛋黃,有的沒有,當作打開粽葉咬兩口才能揭曉有無中獎似的驚喜。後來才知道,原來台灣同學家裡吃的粽子是三角型,餡料“澎湃”(台語,豐富、料多的意思)。媽媽為了解我們的饞,也包起台灣粽。
除了大陸粽(我家的用語,正確的名稱是湖州粽)、台灣粽,媽媽還為爸爸包紅豆粽和白粽子。白粽子的長相是湖州粽,純粹用糯米,豬油都不必放。蒸白粽子時,氣味出塵的清香,打開粽葉,透透亮得像白玉,等不及放涼,拿著半裸包著粽葉的白粽子沾白糖粉,真好吃啊!
我嗜甜食,但偏愛白粽勝於紅豆粽。紅豆粽不好做,攪拌在糯米裡的紅豆,蒸熟時的外皮不能破,內裡又得是綿的,不能有生豆感。紅豆粽沾白糖粉也好吃,可能是小時候莫名的喜歡純淨的白粽,花臉的紅豆粽“長相”略遜一籌吧。
媽媽做菜的“罩門”是只要爸爸沒交待,媽媽就不學;爸爸喜歡,再費神的料理,媽媽都能上手,代表作之一是黃魚麵。買回來野生黃魚,先紅燒蒜頭黃魚,吃了部分較少刺的魚肉後,媽媽再拿下桌,仔細挑去刺,下麵條做黃魚麵給爸爸。沒有湯頭,是黃魚肉拌麵。小孩兒當然也有份兒,但不必另外下麵條,湊著爸爸的麵碗,直接吃爸爸盛在大碗裡的麵才過癮。沒想過、也沒有應該使用“公筷”,分碗不共食的衛生概念。
爸爸晚年生病住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時,不吃醫院營養師調配、健康卻少了美味的餐食。媽媽可累了,得帶自己做的菜、或是買來的料理。我們四兄妹也醫院、餐廳幾頭跑,事前還得知會一下,哪個人今天會帶菜,免得買多了。有次我帶了台北喜來登飯店出名的“雪菜黃魚湯麵”。黃魚片是炸過的,而且黃魚也多是養殖,不是野生的。爸吃了一口,說:“不是真黃魚,這個麵不行,不如媽媽做的。”
爸沒有說要吃豆沙粽,媽媽省了一道功課。吃不到媽媽的豆沙粽,又沒有零用錢,只能巴巴的等著哪家會送上鬥。賺錢了,試了幾家,先是選中台北仁愛路圓環附近“九如商號”的豆沙粽,可是有段時間,不知店家是換了師傅還是出了什麼狀況,味道差了,不如鼎泰豐的豆沙粽品質穩定。而我吃過最“極品”的豆沙粽,是好友、台灣作家王宣一親手調製的。
宣一“文如其人”,文字不炫技、不張揚,樸實有餘韻。宣一文章寫得好,做菜也是一絕。2013年的端午節,她帶著自己包的豆沙粽走進廣播電台送我們,一張口說話,聲音有點沙啞。問她是不是感冒了,她說是炒豆沙的油煙氣太大,燻傷了。宣一的朋友們都是識貨又敢和她開口指定“好貨”的,為了滿足朋友們,一個端午節,她不知得炒幾斤紅豆。
宣一的豆沙粽,糯米軟糯卻仍有勁,豆沙綿細,和白糯米的比例恰到好處。媽媽吃了,也佩服宣一的手藝。我當時想,如果爸還在,一定也會說好。
我把媽媽的稱讚告訴宣一,她先是笑得有點靦腆,然後爽氣地說,“尹媽媽說好,就一定是好的了!”隔年想再拗她的豆沙粽,一想到她炒豆沙的苦工,不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再也吃不到了。2015年2月,宣一前往倫敦看兒子詹朴服裝秀的途中,在義大利山城佩魯賈猝逝。現在吃豆沙粽,總想到宣一,畫面停格在她靦腆的笑容。
其實不管是鹹粽或甜粽,爸都吃得不多,過節時,每款嚐一兩個。我想是粽子太頂飽,不能當下酒菜,少了趣味。爸的口味當然是偏向“外省菜”,但對於台菜,也能欣賞,像是四舅的炒米粉,爸爸的評語是“比媽媽炒得好!”可是他覺得台灣粽就像包了粽葉的油飯,沒有特別之處,不像籍貫廣東省的表嬸,端午節到我家,都要我們幫她蒸台灣粽。表嬸操著廣東腔對媽媽說:“表嫂,粽子‘好食’!”

家裡只有爸和我欣賞白粽子。同學和朋友聽我愛吃白粽多半覺得奇怪,沒有餡料的粽子,有什麼吃頭?同學們都愛吃“尹媽媽包的粽子”,每到端午節,“訂單”就來了。唸大學時,有一次拎著一大袋大陸粽、台灣粽上學,走進大傳系的文友樓,迎面走來教電影的一位教授聞到香氣,停步探詢後立刻說:“我也要!”雖然他的課,我一門都沒選修,隔日還是“有食,先生饌”,帶了十顆粽子給他。
沒有人“點”白粽,媽媽也是象徵性包個幾顆給爸和我。包粽子費工費時,孩子們都大學畢業後,沒有“嗷嗷待哺”的同學們,媽媽就不再包粽子了。台灣是各式料理的大競技場,市面上各款粽子、餡料從最頂級到最傳統的一應俱全。媽媽不包粽子,我們改吃朋友們送的粽子。若有新鮮樣式,或是頂級餡料,像是鮑魚干貝粽,就帶給爸、媽嚐鮮。
爸爸二度中風後,對吃不太起勁,媽媽長年照顧爸爸,犯了幾次憂鬱症,沒犯病時,也不太做功夫菜了。所以我們總想方設法張羅爸愛吃的,希望爸吃得開心,心情會好些。
爸雖然吃得少,舌頭還是很靈。榮總附近有家名氣很大的江浙館,我下班前先打了電話訂乾燒下巴,爸舉筷入口後說,“沒有媽媽燒得好”。媽媽雖然精神不振坐在旁邊看電視,聽爸這樣說,也難得聊起學做燒下巴的往事。至於粽子,因為不好消化,只能嚐幾口,算是應景過了節。
前兩年在台灣我主持的廣播節目裡,端午節前夕,邀請美食旅遊作家吳燕玲,聊聊各地的粽子。燕玲的手藝,不少得自上海祖母,可是上海人竟然沒聽過白粽子。她問,是不是鹼粽?差多了,做法完全不同。開放Call-in,沒想到好幾位聽眾都打電話進來訴說他們和白粽子的童年記憶。好友江才健稍晚傳簡訊給我,提起他和幾位朋友晚餐,恰巧都是我的聽眾,聊起白粽和家裡包的粽子,談得起勁。才健戲謔地下了結論:“一群外省餘孽!”
台北南門市場一個店家,聽了廣播,好心的打電話進電台留言,歡迎我去她家品嚐白粽子。我悄悄去買了,也好吃,但覺得不如媽媽包的軟糯。或許,我真正想念的不是白粽子,而是專屬爸和我的白粽子,那個再也喚不回的時刻:“爸,要不要吃白粽子,我來蒸!”
(作者是台灣資深媒體人,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